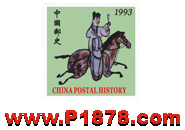1
林冲遇到高衙内的那天是大宋大观四年(1110年)三月二十八日,地点是东京大相国寺门前。
当时正值庙会,有数百人围成一圈看热闹。
圈子中心,林冲抓着高衙内的领子,举拳喝问:“连我的老婆都敢调戏?!我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!!”
林冲这样报名,说明他真的怒了。
平时他自我介绍时总是谦虚地说:“在下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,咳咳…...林冲!”
咳嗽后边是一些他觉得可以省略的内容:其实林冲的真实职务是“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之一”。
这个职位从字面上理解就可以了:为了训练驻守东京的两千来个禁军士兵,东京光教头就有八十万,成功地解决了首都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。
这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可思议,看看禁军编制你就明白了。
林冲上班的地方,东边有间办公室,挂着个牌子叫“洗脚办”。
里面蹲着2000多个教头,专门负责禁军的洗脚问题。
洗脚办后边还有间办公室,里面养着三千多个闲人,上书“搓澡办”。
搓澡办后边是按摩办。
按摩办后边是梳头办——梳头办是个大部门,按每人二十根头发分成无数个班组……
这样一罗列,我个人倒是觉得八十万教头好像还有点不够用的样子。
“我爸是高俅!”
然而高衙内只轻飘飘地说了这么一句,比多少分贝的自我介绍都管用。
“高俅”这个名字如同一声炸雷,把几百围观群众炸的一个不剩,只剩一头驴还茫然的站在原地。
连林冲也虎躯一震,反射似的松了手。
他终于想起,自己的只是八十万分之一。
这里还需要介绍点时代背景。
据历史学家统计,在北宋的盛世里生活着大约一亿人。
当然还有些细节历史学家一般人不告诉,比如说北宋的人口可以分为两类:
一类是富二代和他们的爹,一类是官二代和他们的爹。
剩下的都不算人。
假如剩下的人知道这一点,那么也许这个盛世能够持续时间长一点。
因为那样的话,当他们遇到前两类人时,就会谦虚一些,摆正自己的位置,从而避免很多不自量力的奢望。
可惜这个道理林冲明白得太晚了。
高衙内报老爸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,说明这人的智商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低。
他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,跟二十多年前毫无二致——他的重要性依然只是体现在他是高俅JB里射出来的一个精虫。
假如不是这一点,他连个JB都不是。
当然,衙内受到威胁,不能光指望他拿出户口本来自救——碰上个不关心时事的不知道高俅是谁,他就完了。
于是贴身跟班富安飞一般的跑进尚书省找高俅报信。
富安在高府级别很低,没来过这里,不知道高俅值班的兵部在哪。
幸好沿途有无数路牌带着箭头的路标,上书:“有关衙门”。
只要你在北宋生活过,就应该知道,“有关衙门”是大宋最神秘的机构,神秘到有事的时候谁也找不到它的地步。
富安沿着指示方向走到底,看到的是数座一模一样的建筑,大门紧闭,门口挂着一模一样的门牌,上书:“我不是有关衙门”。
他这才明白,原来“有关”是“有事就关门”的简写。
他只好挨个大殿敲门:“搅扰则个!高殿帅在吗?”
这里需要对宋王朝的朝廷架构做些说明。
当时的尚书省是名义上的行政机构,分为六个部门:
其中有负责修路搭桥然后再把它们拆掉的工部;
有负责解释法律对什么品级的人不适用的刑部;
有负责提拔一批贪官然后再把他们换成另一批贪官的吏部;
有负责每年铸币上万亿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户部;
当然,还有负责维护稳定的兵部,
以及宣布以上现象均不存在的礼部。
在六部的共同努力下,北宋终于在灭亡前20年宣布进入了盛世。
由此可见,北宋的六部里面属着礼部最忙。
偏偏富安第一个敲的就是礼部的门。
当时给事中(办事员)们个个焦头烂额,忙着写稿子。
什么“去年共铸钱四万亿文,通货膨胀对百姓生活影响不大”啊,“各路(省)大旱并非黄河大堤导致”啊,“去年共处分贪赃官员上万名,仅占朝廷命官之百分之一点五,证明反腐无用论毫无根据”啊,“吏部侍郎反驳我国官员过多论”,等等等等。
就连领导都没闲着,60多个侍郎(二把手)正群策群力写一篇重量级社评,“大宋岁赐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”。
文中着重强调,大宋在崛起之后的今日,仍然坚持赐给周边国家的岁币,证明了大宋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......
于是富安刚露头就被轰了出去,只好又原路跑回去。
其实他本来不用费那么多事,高俅就在事发现场不远处。
从大相国寺沿着御街往北,不远处就是刚刚修缮完毕的樊楼。
装修的钱是朝廷出的,准确地说是徽宗命令朝廷出的。
原因很简单,李师师需要一个地方卖唱。
徽宗和李师师的关系我不说你也知道,当然了,大宋臣民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。
因此尽管樊楼被徽宗御笔赐名为“国家大剧院”,但老百姓坚持称之为“国家大妓院”。
在樊楼的雅间里,朝廷重臣和徽宗皇帝都身着便服,正在与民同乐。
刚刚在早朝上含泪保证“一定要稳定房价”的太师蔡京正手捧徽宗的新画啧啧赞叹:
“传世之作!求官家割爱——老朽愿意用京西六所宅院来换……”
高俅当时跟一位特殊人物坐在一桌——遗民盟主席,后周世宗嫡系传人,禁军名誉通侍大夫(少将),小旋风柴进刚从横海郡到达东京,参加一年一度的春祭。
当时大宋宣布培育出了第五代杂交战马,惊动了东亚三国,他正在就此事做祝酒辞:
“杂交战马么,这个怎么说呢,我考虑到,观察了很久,这个杂交战马,杂交战马呢,怎么说呢,他还,杂交战马从,我认为啊,咱们从严格意义上,他也是受杂交的战马,当然他的这个作战质量,他肯定不亚于这个纯种战马的这些东西……”
这段讲话依然以柴少将的标志性口头禅结束:“再加上我老爷爷的思想,肯定能打到上京(辽国首都)......”
高俅在副陪座上哭笑不得的陪着笑脸,此时传来了的高衙内的呼声。
大家都愣了。
片刻,一个千绝代佳人走了进来,坐在徽宗旁边,说道:“奴派人打听过了,原来是高殿帅的公子,又看上了谁家的娘子……”
说这话的就是樊楼的头牌,我们熟知的一代名妓,当时的官方承认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李师师。
徽宗听罢,带头哈哈大笑。
然后包间里的重臣们笑成一片。
高俅看着同僚们揶揄的目光,也报以似笑非笑的表情,说:“小子胡闹,诸公见笑了。”
他心里想的却是:妈的我儿子终于也有今天了。 |
|